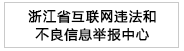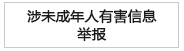醉鱼草的毒(散文)
□ 王微微

能将鱼醉倒的草,一定是有毒的。
有毒的草十有八九能入药,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言之“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
老一辈的人说,山野百草皆入药。生活在沟沟坎坎里的他们,接近神农,有伤风感冒虫叮蛇咬什么的,一般不会去医院,直接去山里摘一些花花草草,煎服几次病就去了。甚至有一些西医挥针动刀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用农村的土方法捣鼓起来,吃着吃着病就好了。有时候觉得,这草药比起西药,温文尔雅多了。
醉鱼草属马钱科灌木,4至10月开花,8月至翌年4月结果。扎堆开花扎堆结果,“穗状聚伞花序顶生”,芳香传远,微毒,我戏称其为“一平方英寸的毒药”。
美国声音生态学家戈登.汉普顿著有《一平方英寸的寂静》,那是他为了声音环保而发出的警语。我这“一平方英寸的毒药",是心里花园的香水。香水有毒。
记忆中,小花园右泥墙上长着一株醉鱼草,应该说是一簇,好几根粗枝条重叠交织在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开着细微繁复的紫花,蜂鸟虫蝶与花,一起从墙头垂挂下来。你不用为它费多少心思,它是自生自长自灿烂的,为小花园添加了不少颜色。
农村山涧溪沟,田头地角到处都有这种花,它们侧身而立,挤拥在一起,非主流身姿,燃烧紫色的火焰。远远地看,乘风徐来,像是身披紫纱落地长裙的女神飘过来,看得人心尖晃呀晃。那些紫,从粉开始,浓浓淡淡,浅浅深深,从自然朴素里渐渐生出一朵花的气质来。紫色尊贵,代表着吉祥美好,在古人眼里,紫色还是权力的象征,所以一直为皇宫贵族所尊崇。
有些勤劳却没有情趣的农人,常常在除草的时候,把田头角落的花花草草一起除了去。这也怪不得他们,在还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一切“侵略”庄稼的,都是错误的,都是要被打倒的。
当然,有情趣的人也不少。他们在侍弄庄稼的时候,也舍不得花花草草。这样,他们的农田就比别人的农田活得滋润些,春花又秋月;这样,他们干活累了,坐下来喝一杯水,抽一根烟的时候,就可以和一朵花默然相对;这样,他们的生命辞典里就没有“斩草除根”的残忍。
凡是花,大都是踩着枝头昂首向上绽放的。凡是生物,不同程度上都有炫耀的倾向?比如舞台上的模特,踩着五寸高跟鞋,袅袅婷婷走来走去美给你看,我们在底下仰望,真美啊!这羡艳里有着距离。当然,她们都是美的引领。
醉鱼草是低到尘埃里开花的。它也有漂亮得体的“衣衫”,也有最美的S型曲线,但它不炫,它是收敛的。在它最美丽灿烂的时候,也是它离泥土最近的时候,那恭敬虔诚的身姿,犹如紫衣女神俯首阅读大地。山风拂来,衣袂飘飘,“闭月羞花人皆叹,落雁醉鱼妒红颜”,不知不觉间,这弯腰开花,竟开出了精神与信仰,开出了秀气与贵气。
物各自我,尽其用。
我生活在河边,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村里的人会相约去河里“药”一次鱼,弄点河鲜,以改善伙食。这药,不是药,是山茶榨油后的渣饼。捣碎,撒入河里,不一会儿,那些鱼,便醉醉醺醺,从水底下直往上蹿,耍起花样泳。大大小小的人,手里拿着网兜,肩上背着鱼篓,守在河流的两岸眼疾手快地捞。流水一直在走,人们顺着流水捞。深潭静流处,水至清,有大鱼,状态清醒。大人们有经验,知道是“药力”不够了,就会在附近,扯一捆醉鱼草,捣汁洗下去,不一会儿,那些水底的大鱼便不胜酒力了,摇摇晃晃,翻起白肚皮,成了鱼篓里的大俘虏。
小朋友喜欢模仿,夏天午后,趁大人午睡不注意,偷偷约起来去挖醉鱼草,结伴去门前小溪沟里药鱼。大人有大人的乐趣,小孩有小孩的清欢,各自欢喜。鱼不欢喜,人类也“有毒”。
百花百草百语。醉鱼草的花语是信仰心。
一朵有信仰的花,才是带花骨的花。推及之,一个有信仰的人,才是有灵魂的人。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才能顶天立地巍巍然。
这醉鱼草,是鱼的一杯野果子薄酒。喝了后,东倒西歪,摇摇晃晃,一时间找不到水晶宫的大门。
这醉鱼草,是我童年记忆里的一杯乡愁,性温,有毒,忍不住要偷偷地喝一口,却不曾想,一喝就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