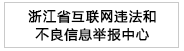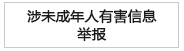名胜的文化记忆与诗人的心灵建构
——周必大《过庐山吊大林》发微
□ 张谦
摘 要:文本化是名胜进入文人审美视野后自然而然的历程,名胜的文本化书写赋予了名胜深刻的文化内涵。当名胜的物质实体消亡后,文人再度题咏,便形成了文本化的名胜。即使时空流转,以名胜为中心的文化内涵存在于名胜书写的历史记忆空间中,不断沾溉着后人。大林寺始建于晋,自唐以来,不断为诗人赋咏,白居易赋予了大林寺深刻的文化内涵,齐己继踵题写,不断层叠,使得大林寺形成了特定文化记忆的“空间”,南宋周必大创作的《过庐山吊大林》标志着大林寺在毁灭后成为文本化的名胜,在前贤创造的大林名胜的文本风景空间中,周必大体认前人,映照自我,在诗歌中构建出饱含文化记忆和自我经验的心灵世界。以大林寺为例,考索名胜景观与文学文本、诗人心灵的互动关系,进而由此及彼,阐释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其他案例,对于文学地理学和原型诗学的阐释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映照意义。
关键词:周必大;《过庐山吊大林》;名胜;文化记忆;心灵
一.引 言
名胜,作为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审美对象,很早开始便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文学景观。山水、隐逸、咏史等类型的诗歌中有相当可观的比例以名胜为题材,诗人在以我观物和以物映我的方式中获得审美的快感和思想的升华。名胜又可以分为自然名胜和历史名胜,但是无论何者,任何美的发现都是依靠人的眼睛和思想。对于自然名胜,人在主观能动性下的审美视觉给予他们了历史与文化的地位,“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对于历史名胜,在历史的时空中为历史人物所建构,其历史文化内涵一开始便获得并承载下来,后世文人的不断发现与层叠,更加坚实的奠定了历史名胜的地位。可以说,文人的题咏不仅赋予了某地以名胜的意义,而且文人的题咏不断地增加了名胜的文化内涵。
自然名胜亦或历史名胜,自从文人赋予他们了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后,就不断进入文人的作品中,呈现出名胜的文本化;而,当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某些名胜的实体不复存在后,后世的文人在前人题咏的文本经验上,继续追寻和题写,又形成了一种文本化的名胜,商伟教授对此论述颇为精深。无论名胜的文本化,还是文本化的名胜,都是文人以名胜为中心进行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当某一特定的文化活动或者历史事件以名胜为中心而开展,这个名胜也就获得了这一特定的文化内涵,成为一种文化原型,如乌江(包含乌江亭)名胜,自从项羽兵败于此,便获得了相应的文化内涵,后世杜牧《题乌江亭》、王安石《乌江亭》、李清照《夏日绝句》等诗依旧以项羽兵败之事为内核,承继着乌江名胜的文化内涵。具有文化原型意义的名胜将不同诗人的同题书写纳入同一历史文化体系中,即使千年时空流转,名胜不复存在,但是如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一书中所论:“真正重要的是地点本身,而不是在那里作为过去的遗留物还能找到的物体”,“名胜”本身及所处空间蕴含的文化记忆,依然能够沾溉游览“名胜”的后来者。大林寺是庐山群体名胜风景中的一员,其历史的消涨是名胜的文本化走向文本化名胜的过程,在名胜的文本化风景下,南宋诗人周必大在大林名胜为中心的文化记忆体系中追寻和体认前人。笔者不揣谫陋,欲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南宋诗人周必大《过庐山吊大林》(后文简称《吊大林寺》)诗入手,观照大林名胜的演进历程,进而在此基础上探究文本化的名胜形成后对诗人心灵建构的意义,为相关研究提供个体实例阐释。
二.文本化的名胜形成:从白居易到周必大的大林寺书写
大林寺与东林寺、西林寺,合称庐山三大名寺。庐山不仅是风景优美的名山胜地,而且在宗教史上占据着显赫的地位,自晋朝以来,名寺林立,高僧云集,无比兴盛繁荣,寺庙有归宗寺、东林寺、西林寺等,高僧有达摩多罗、慧永法师 (慧远同门师兄)、善导大师等。大林寺相较于东林寺、西林寺等寺庙并非声名显赫,然而考究历史文献,大林寺在宗教史与文学史中仍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众多高僧与此寺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诗人游览时留下了多篇脍炙人口、享誉古今的经典诗篇,由此观之,无论宗教意义,还是文学题写,大林寺作为名胜景观的历史地位早已确立。“中国历史上的名胜之地,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书写的产物——书写赋予它以意义,也规定了观照和呈现它的方式。它被文本化了,而且通过历代的文字题咏和评论,形成了自身的历史。”观照大林寺的历史隆替与文学书写,正可考索大林寺从名胜的文本化转向文本化名胜的过程。
大林寺的历史形成,据史料所载:
大林寺,在庐山之巅,有上、中、下三寺。
上大林寺,在庐山之巅,晋大元间开创,元末兵毁,我朝(明)宣德九年,天池寺僧圆究,成化间僧园泰,相继增修。
东林寺之北有大林寺,十八高贤中昙诜所建也。
据上可知:第一,大林寺地处庐山之巅,并非为独立的单座寺庙,而是分为上、中、下三寺,三寺合成大林寺,周必大所吊为上大林寺(后文所言大林寺皆指上大林寺)。第二,大林寺历史悠久,(上)大林寺为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为东林十八贤之一的昙诜所建。昙诜法师,南北朝时代宋国广陵人,幼年即出家,为远公(僧慧远)弟子。晋昙诜创寺之后,多位高僧先后止于大林寺参禅悟道,广布佛法,《续高僧传》载隋代高僧释智锴,“晚住庐山,造大林精舍,缔构伊始,并是营综。末又治西林寺。两处监护,皆终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馀载,足不下山,常修定业。隋文重之,下敕追召,称疾不赴。后豫章请讲,苦违不往,云:‘吾意终山舍,岂死城邑?’道俗虔请,不获志而临之。未几遂卒于州治之寺,时以为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业六年六月也。气属炎热,而跏坐如生,接还庐阜,形不摧变,都无臭腐,反有异香。道俗叹讶,遂缄于石室,至今如初焉。”释智锴在大林寺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建造精舍,经营治理,使得大林寺的面貌焕然一新。受隋文帝征召后,释智锴仍然抱朴守道,称疾不赴,彰显出得道高僧的操守与禅定。其后,当时有太原王姓僧侣释慧云,“远祖避地,止于九江,投匡山大林寺沙门智锴而出家焉。”无论皇帝征召,抑或远僧来奔,都体现出释智锴的宗教影响力,也奠定了大林寺作为名胜风景的历史地位。
大林寺第一次从实体名胜进入文学文本是在隋末唐初,初唐文学家虞世南为大林寺作碑记,时光流转,惜未留存。将大林寺真正意义上从山岭丛林推向诗文文本、从宗教名胜转作文学景观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唐宪宗元和十年(815)七月,白居易因上疏宰相武元衡被盗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白居易谪守江州时,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闲暇之时得以游览庐山之巅的大林寺,并写下《游大林寺序》(以下简称白《序》):
余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广平宋郁、安定梁必复、范阳张特、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士坚、利辩、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东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是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口号绝句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既而,周览屋壁,见萧郎中存、魏郎中弘简、李补阙渤三人姓名诗句。因与集虚辈叹,且曰:“此地实匡庐第一境,由驿路至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寞无继者。嗟呼,名利之诱人也如此!
时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乐天序。
白《序》中口号绝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后世题为《大林寺桃花》)是白居易对海拔不同、气候变化影响植物生长周期的直观感受,“诗歌作为人文的一部分,正是文经由心与言的媒介而产生的自内而外的彰显,而不是对任何外在对象或客体世界的模仿与再现。”考究白居易的江州贬谪始末,《大林寺桃花》一诗表面言地理高低而春花相异之事,实则言白居易贬谪江州后官位高低迁改、上下变易的逆旅沧桑。《游大林寺序》记载了白居易游览的随行人员、游览路线,并且重点叙述了大林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气息。“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此句描绘出大林寺穷远静寂、清旷凄幽的自然美。“既而,周览屋壁,见萧郎中存、魏郎中弘简、李补阙渤三人姓名诗句。”此句则记述了唐人的题诗盛况,萧存、魏弘简、李渤皆为唐时名士,游览寺壁题诗留名,增添了大林寺作为名胜景观的深厚文化底蕴。
《游大林寺序》中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往昔历史与今日游乐相交织,正言明大林寺于唐时的繁荣兴盛,故而白居易赞叹其为“匡庐第一境”。“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认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容易令人信服。”白居易创作的诗与序,为遗落在庐山之巅的名胜古刹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和血液,使得大林寺自虞世南碑记,萧存、魏弘简、李渤等人题咏后,再次从山水静默走向了文本题构,文学空间的属性逐渐增强,成为后世诗人追索的足迹。晚唐时期,大概是因穷远的地理位置,大林寺在“会昌法难”中未曾受到侵扰,著名僧人齐己登临庐山大林寺时,观白居易所题诗文有感而作《登大林寺观白太傅题版》:
九叠苍崖里,禅家凿翠开。淸时谁梦到,白傅独寻来。
怪石和僧定,闲云共鹤回。任兹休去者,心是不然灰。
虽然齐己相对白居易而言是题写大林的迟来者,但是并未像李白与崔颢一样因黄鹤楼一诗成为竞技者,将大林名胜当作竞技的场域,因为齐己“并不是以他的作品颠覆前作或替代前作,而是与之形成了不可分离的互文关系。”诗歌尾联中“不然灰”意指失势的人,在佛家语中可指高僧的禅定修为,但是齐己的诗歌是对白居易题版的体认,所以就并非仅仅停留在禅意层面。“访寻或登览一处名胜古迹,就是接受一次题写的邀请,而题写又意味着加入前人的同题书写的文字系列,与他们进行想象中的对话。”白居易在序文中并没有直接表达贬谪失势之意,齐己在观照白居易的文本时,体会到了诗人诗文中的心灵风景,加入了同题书写的文字系列,与他进行想象的对话,对白《序》进行了阐释与补足,两者一前一后的题咏将它们共同纳入了一个共享的互文空间体系中,这也白居易赋予大林名胜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刻。自晋代昙诜创寺,隋释智锴等僧侣缔构营综,至虞世南作碑记铭之,大林寺作为名胜的地位不断被夯实,但是在走向文本化的进程中,是白居易的诗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齐己与之互文关系的诗作,进一步推动了大林名胜的文本化。
此后,北宋时期游览庐山大林寺的文人墨客亦为数不少,使得大林名胜更加高度的文本化。嘉祐六年(1061),著名理学家周敦颐“三月十四日,自虔赴永,同宋复古游庐山大林寺”,写下歌咏大林寺的两首诗歌:“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盘层顶上,人在半空行。水色云含白,禽声谷应清。天风拂襟袂,缥缈觉身轻。”(《游大林寺》)“公程无暇日,暂得宿清幽。始觉空门客,不生浮世愁。温泉喧古洞,晚罄度危楼。彻晓都忘寐,心疑在沃州。”(《宿大林寺》)大林寺山房温暖、林花鲜艳,水清云白、禽声清脆,风景优美、环境清幽,诗人游览、眠宿于此,感觉心旷神怡,不禁有萧然出尘、脱俗忘我之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游庐山宿大林寺,“癸丑,过东、西林寺,与道士任禹恭、丁宗元、僧本全俱过化成、护国、石盆寺、宝兴岩,宿普照寺。甲寅,止峰顶、大林、天池寺、佛手岩,至定心石,还大林寺宿。乙卯乃归。”两宋之交的王廷珪游庐山观览寺中鑱刻,“复从岩东北下三里至宝林,即唐大林寺,白乐天尝序此地,实羌庐间第一境。人迹罕至,古今识游者鑱刻未泯也。”北宋时期的庐山大林寺依然延续着隋唐时期的辉煌,文人墨客游览庐山多寄宿大林寺,题咏书写,络绎不绝。
至南宋前期,大林寺毁灭,失去了名胜的物质实体,周必大于《泛舟游山录》中有详细的记载:“……自佛手岩一二里渡小溪,乃至大林,寺遭野火仅有基址,其额为冯教练者徒寘坟庵,并令一僧据其田,人无知者。予按白乐天诗,心实慕之物色,乃能至。其旁小径即下山南楼贤路也,地在山顶而反平衍,谢灵运诗云:“冬夏共霜雪”,其高可知。予作吊大林诗:上尽诸峰地转平,天低云近日多阴。古来南北通双径,此去东西启二林。虞世南碑从泯没,白居易序合推寻。匡庐第一金仙境,忍使如今遂陆沉。”藉此可知,大林寺遭受野火焚烧,前贤所建精舍等都已焚为灰烬,寺额田地亦为他人据占,仅留基址等断壁残垣。兴盛千年的古寺遭遇天灾人祸,昔日的兴盛辉煌转变成今日的破败萧索。周必大面对残存的大林寺遗迹,并未因实体对象的消亡而无从入手进行吟咏凭吊,因为“过去是由词语,而非石头构成的。”大林寺已是前人题写文本中的符号,存在于虞世南碑记中,存在于白居易的序文中,也存在于齐己等诗人的文学文本中,“文本化的名胜建构与名胜之地的历史平行交叉,并且从根本上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的名胜形象,但并不依赖于名胜古迹的物质实体而存在。”而且,即使对于未曾观览的人而言,名胜的形象模糊不清,“但是凭借文学的描写,人们会由此而生发出丰富的联想或者想象,于是这些景观的形象便在脑海里浮现,变得集体可感。”周必大在名胜的物质实体不复存在的基础上,回瞩大林寺的历史流变和文学题写,撷取虞世南和白居易两人有关大林寺的典型文化事件,在大林寺的文本记忆上题写名胜,将大林寺千年的时空沉浮与烟火消涨纳于片章,用文字砌成一座饱含文化记忆的文本化的大林名胜。
三.“名胜”的文化记忆与周必大的心灵建构
文人对某一名胜的同题书写,在符号化的名胜周边形成了一张具有共同向心力的空间网络,无论后世的文人如何创造,也仅仅是因个体经验的相异而稍微的向外延展,却很难挣脱这张网络,从而自觉或不自觉的在文本中书写前人的经验与记忆,因为名胜不仅“能够通过把回忆规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尤其是当后来者的经历与先行者的经验高度重合时,先行者在诗歌中题咏的浸润着文化记忆的名胜风景,即使实体不复存在,成为文本化的名胜,但是曾经承载名胜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不断阴翳着后来者的创作。《吊大林寺》一诗若从文本及《泛舟游山录》所载创作缘由的理解,诗歌流露出周必大目睹大林寺遭受天灾人祸而叹空成迹后的惋惜、无奈之情,其思想主题应是显而易见的凭吊咏怀诗,然而考镜源流,结合大林寺成为文本化名胜的演进历程和文化意蕴,追索周必大仕宦履历的草蛇灰线,可以发现周必大诗中的独特心灵洞天。
周必大自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及第之后,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南宋孝宗即位时,周必大即任中书舍人,成为天子近臣。然并未许久,南宋孝宗改元隆兴后,欲任命潜邸时期的亲信曾觌和龙大渊为知閤门事,群臣反驳,《宋史》记之甚详:
绍兴三十年(1160),以寄班祗候与龙大渊同为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禅,大渊自左武大夫除枢密副都承旨,而觌自武翼郎除带御器械、干办皇城司。谏议大夫刘度入对,首言二人潜邸旧人,待之不可无节度;又因进故事,论京房、石显事。大渊遂除知阁门事,而觌除权知阁门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进之,何面目尚为谏官?乞赐贬黜。”中书舍人张震缴其命至再,出知绍兴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论二人市权,既而给舍金安节、周必大再封还录黄。时张焘新拜参政,亦欲以大渊、觌决去就,力言之,帝不纳。焘辞去,遂以内祠兼侍读。刘度夺言职,权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阁门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寻与祠,二人除命亦寝。
此次君王与臣子的权力博弈,宋孝宗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虽台谏交章,终未改变君王之意。周必大拒不书黄,并进《缴驳龙大渊曾觌差遣状》,孝宗斥为朋党。故周必大坚决乞祠,以示气节:“求一宫观差遣,仰以释圣上朋党之疑,下以解二人报复之怨,此上策也。某非不知思权时之宜,为调停之策,但若不决去,则此辈必谓士大夫可以爵禄诱,可以威命胁。一堕其计,人主信之愈坚,任之愈笃,祸发萧墙,毒流华戎。”唯有通过此举,让君王“知士大夫之不可轻,近习之不可亲。”在周必大的反复决绝请求之下,隆兴元年(1163)三月,孝宗准奏,敕周必大主管台州崇道观。宋代祠禄制度自北宋真宗时期创始至南宋时期发生了极大变化,南宋时期奉祠官员虽俸禄尚优,然政治地位降低。〔22〕周必大自位居中枢的中书舍人任上而出外奉祠,其中政治地位之升降自不待言,故而周必大奉祠虽无贬谪之名,却有贬谪之实。
周必大奉祠返乡后,徜徉山水,交游唱和,高吟“此去读书真事业,向来正字误根银”,流露出深切的仕宦反思和闲居自得感。然而古代士人在遭受挫折与磨难时,几乎未有可以泰然自处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周必大作为宋代儒家士子的典型代表,自然难以独善其身,纵览周必大奉祠期间的文学创作,闲居自得的吟唱只是偶尔的自我安慰,心中更多的是魏阙与江湖、仕进与贬谪的矛盾。
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周必大居乡忆及去年会庆节之乐,作小诗一首咏怀:“去岁兹辰侍赤墀,诏黄亲许奉瑶卮。如今不及封人贱,犹对君王效祝辞。”去岁为绍兴三十二年(1162),周必大仍于朝堂侍奉君王,君恩正隆,而此时奉祠闲居,不及封人恩遇,心中不禁有酸楚、黯然之感,今日追忆昔日之恩遇,正是对昔日恩宠的怀念与对当下的牢骚。
乾道元年(1165)四月,周必大作《故翰林汪公端明居零陵时,尝作玩鸥亭,今彊中提干敬以其榜揭荆溪第中,命某赋诗》,诗歌首联“贾生问鵩谩伤神,应愧先生入理深。”贾谊作为中国古代贬谪诗人的文学典型,周必大歌咏贾生,正是借古人之事哀吊己身遭遇。
诸如以上事迹与文学活动在周必大奉祠期间不胜枚举,鲜明的彰显出周必大性格中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中国古代士人传统,也是周必大在山水清音中杂糅的不平之鸣。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此时距隆兴元年(1163)周必大奉祠归乡五年有余。宋代祠禄制度规定“百官奉祠禄者并以三年为任。”“除宫观者,毋过两任。”以常理推论,周必大即将结束奉祠、磨勘高迁,然而宋代祠禄制度规定并非按部就班、一成不变,与周必大同时代的诗人陆游与朱熹奉祠期间,虽祠禄期满,朝廷却未起复。“放翁自严州任满东归后,里居十二三年,年已七十七八,祠禄秩满,亦不敢复请。”故而陆游作《祠禄满不敢复请作口号》三首以陈心迹。“浙东监司朱熹,以言台州守臣唐仲友而畀祠禄,至今六年。朝廷藐然不省,亦废然不用,天下屈之。”陆、朱二人作为宋代祠禄官制度施行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名人典型个案,史书未载的其他案例更不知几何。由此可见,祠禄官的磨勘迁改并非抱令守律,而是有着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周必大正处奉祠末期,心中滋味可想而知,“文人在遭受贬谪时悲愤不平,孤独忧伤,但仍然执著于追求理想,直面人生。他们矛盾复杂的内心感情与感受,使贬谪文学具有丰富深邃的内涵。”有鉴于此,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末,周必大于奉祠即将结束之际游览庐山大林寺作《吊大林寺》诗,并非是单纯的对大林寺今昔兴衰的凭吊,而应融汇了诗人情感、理想的复杂感受。
- 从大林寺的物质实体迁改而观之。《吊大林寺》诗中“匡庐第一金仙境,忍使如今遂陆沉。”此句诗脱胎于白居易《序》文中“此地实匡庐第一境,由驿路至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寞无继者。”大林寺作为匡庐仙境,兴盛千年却遭野火一朝毁灭,仅留基址,令人无限感叹,寺庙建筑重建与否又茫然未知。考量周必大奉祠始末,周必大由朝廷之栋梁,君王之臂膀,骤逢时变而奉祠归乡。宋代祠禄制度的偶然性,又让周必大对奉祠期满进而磨勘高迁的前程倍感惆怅,流露出不甘陆沉的生命精神。在周必大看来,大林寺的兴废陆沉与自己的贬谪升降何其相仿,诗人的精神已融入大林寺由兴转衰的历史变迁时空中,大林寺成为诗人个体生命的知己与映照。
第二,从大林寺蕴含的文本化的风景记忆而观之。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中“诗言志”之说,早已为历代文人接受与体认,所以后世对前人作品的理解不会停留在作品本身,而是通过作品探寻文本背后的人生遭际、思想变化和生命精神。“文学的思想性和文化内涵,更会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现实、自然和人生的某些感悟,或者追寻。”《吊大林寺》诗中“白居易序合推寻”,是周必大的情感世界与白居易仕宦心态的映照与共鸣。唐宪宗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盗杀,白居易因上书言事,触怒执政奸佞而遭恶言,随后由太子左赞善大夫贬谪为江州司马(前文详尽,兹不赘述)。江州贬谪期间,白居易作《游大林寺序》(含诗)题咏大林寺,“自然界的诸般物色的姿态和‘文章’,经过这一番观照与书写,一方面被文本化了,也就是被组织进诗行、对仗和诗篇整体的文字结构,另一方面则转化成为意象和意境,变成了文本化的心灵风景。”白居易的《序》和诗蕴含着贬谪后哀怨愤懑与不可言说的伤感,在文本中形成了自我心灵情感的风景空间。至周必大游览时,虽然大林寺已经毁灭陆沉,但是白居易文本中的心灵风景早已化为记忆存留在名胜的文化空间里,“记忆在过去和现在的缝隙中架起了桥梁”,周必大言大林寺的遗存自然风物与白居易《序》文相合,不仅是当下风景与历史记忆的吻合,更是贬谪心态下自身经历、情感对白居易文本化的心灵风景的推寻与映照,白居易创造的文本化的心灵记忆风景不断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阴翳着周必大。
言而总之,“名胜楼台的名称被抽空了具体所指的特殊性,从而变成了一个漂浮的能指符号。无论具体的情境如何千差万别,也无关登览与否,所有题写名胜的诗人,都生活在互文关系所结成的这同一张意义网络之中。”在白居易、齐己以大林寺为中心构建的互文关系所结成的同一张意义网络之中,周必大面对“大林名胜”,在文化记忆编织成的网络空间里,思考南宋的政治环境和自我遭际,从而在诗歌创作中建构心灵世界,彰显出贬谪闲居的愤懑哀伤和不甘陆沉的生命精神。
四.余 论
周必大创作《吊大林寺》之后不久,自乾道四年(1168)四月开始,奉祠六年的周必大官职屡迁,从奉祠闲居多年、拖延任职地方到调任朝官,也是南宋士人精神影响下的周必大与朝廷博弈的胜利。〔32〕大林寺在周必大游览之后,后世重新建构,不断修缮,虽然据现存文献已不可知晓大林寺重建后具体的面貌,但是可以推知,后世不可能凭空想象名胜的历史形象,而是需要通过文本的历史书写进行整合构造,从文本化名胜的空间记忆中再次衍生出实体的名胜风景。
如今,在历史光阴的消磨下,大林寺虽已叹空成迹,然而大林寺作为名胜而蕴含的历史形象和文化内涵依然浸润长存于“大林寺”的名号中,以周必大等为典型形象的中国传统士人品格、政治形象与生命精神依然闪现在大林寺的历史空间中,大林寺昔日所承载的高僧禅音、佛教盛会也在如流不居的历史云烟中激荡回响。因此,以大林寺为例透视大林名胜的历史时空和层叠内涵,对于我们由此及彼的观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中国文学时空中单个名胜和群体性名胜的文本书写、文本化名胜形成的历史以及文本风景下的诗人心灵世界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