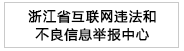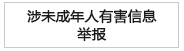“担大峃”
王景贤“担大峃”在黄坦已有千年历史,我们正好赶上它的末年,因为第二年黄坦就通车了。在未通车以前,由于不便水路,物资的来往只能在大峃与河背两地水路中转,再用肩挑,所以,黄坦人在大峃、河背来往挑物资叫“担大峃”、“担河背”。
那是1965年7月的一天,我们结束了小学五年级的最后一节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与第七份的阿宽、第四份的小林和对门的苏东,规划着暑期怎么去赚钱为下学期准备买学习用具的事,我们想来想去,那时的赚钱方式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为供销社到大峃把物资挑进来,叫做“担大峃”,或为粮管所将粮食挑到河背去,叫做“担河背”;二是找个工程队参加修建公路,这是大人干的活。我们只有“担大峃”或“担河背”。
“担大峃”的头天傍晚,我选来一根爸爸挑担用的拄杖,因为太长,把它锯掉一截,又在爸爸的扁担上绑好千斤绳,试了试刚好,又去帮助对门的苏东做了一根。阿宽与小林各自还编织了一双草鞋。
因为大峃距离黄坦二十五华里,山路崎岖,回来要爬10里的长岭,需要早早起床。鸡鸣二遍的时候,我便叫妈妈做饭,自己去叫另外三个同学。趁着朦朦胧胧的月夜,到了第七份老宅,经过上间,便是漆黑一片,阿宽家又在上间后面的后省,由照正壁所隔,后省通常是放置死人之处。我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门,沿着上间用一双颤抖的手摸着板壁,胆战心惊地跨过了照正门槛,摸到他家的门,立马“阿宽起床,阿宽起床”叫着,与其说是叫人,还不如说是为了壮胆。惊醒全屋百来号人,可是,那时的人都能理解,不会有任何人埋怨。
吃过早餐,我们扁担上挑着鼓鼓的饭包,深一脚浅一脚地上了际坳塘,天才蒙蒙亮,到了大峃黄坦供销社采购站,坐在门口等了将近两个小时,王经理终于来上班了,一见我们坐在门口就说:“娒,今天没有货担呀!”我们一下子给懵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四双乞求的眼光同时向王经理投去。善解人意的王经理挠挠头说:“那这样吧,你们既然来了,就挑一些盐去吧。”我们立即兴奋了起来。只见他打开盐库,指着潮湿的地上一堆黑黑的、湿漉漉又沉甸甸的麻袋说,你们各人去拿两只麻袋,能挑多少装多少。阿宽装了60斤,我装了50斤,小林与苏东各装了40斤,我把王经理给的出货单装进口袋。兴高采烈地挑起担子往回走。开始,我们百米一撑,还比着谁有能耐。
中午时分,我们翻过了程坳门、穿过了五十二街,跨过由自然溪石垒成的中堡溪水,挑到了中堡,身上不知流了多少汗水,反正衣服,裤子全是湿漉漉的,犹如刚从水里钻出来一般。
透蓝的天空上那轮白白的不像是太阳,而是一团燃烧的火球,我们盼望着云彩,可它早已被太阳烧得无影无踪,我们盼望着路边的树能给我们遮一下,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可它卷着叶子垂下头,无精打采地立着,自身难保。大地是死一般的寂静,寂静的只有那知了,能在树叶底下避着烈日,享受着那一点阴凉,可它还不够满足,仍然在“热死了,热死了”不停地哀叫。
我们肚子早就闹革命了,可还是艰难地挑着,寻找着有个遮阴的地方安慰一下肚子。终于,在中堡百步岭脚,看到了一个涵洞,我们赶紧将担子靠在滚烫的石壁边,各自拿着饭包,双手着地爬了进去。那种清凉绝对胜过现在的空调。我们打开饭包,狼吞虎咽地啃过几口番薯丝团后,才发现苏东全是白白的米饭,干菜里还夹着一小块肉,因为只有他爸爸不是种田的,是一个小学老师。我们平时都非常羡慕他。这次他能跟我们一起来,完全是为了兴趣,体验生活来的。其余两人所谓的菜,都是几根黑黑的腌咸菜,我还有一个咸蛋呢。饭过半,因为口渴,实在是咽不下去了,我们只得到路下的小溪里喝几口溪水,可溪水也是烫的。管它呢,我们纵身一跃,连衣带鞋,跳进了齐腰深的溪潭里戏了一番,浑身感觉说不出来的轻松。回到涵洞,吃完那剩下的有点生硬的番薯丝团,依依不舍地钻出了“空调洞”。继续挑起那沉重的担子,开始上那10里的长岭。
刚刚开始的那段百步岭,也许是享受过“空调”和戏过水的原因,我们还能几十步一撑,到了后来,不但是十步一撑,还十步一歇。
放下担子,浑身是那么的轻松,没有涵洞、没有树荫。午后的太阳像个大火炉,斜面烤来,把大地烤得像烧透了的砖窑,冒起白烟,一丝风也没有,稠乎乎的空气好像凝固住似的。趴在路边家里泥地上的那条大黑狗,嘴里流着白沫,吐出一条长长的红舌头,气喘吁吁的动弹不得,何况我们这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儿,暴晒在烈日底下,肩上还挑着几十斤的盐呢。
不得已,我们席路边草地而坐,有的还大字形展开躺在草地上,草地像刚出笼的馒头,滚烫滚烫的。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右脚底好像有点痛,一看,原来是鞋底破了一个大窟窿,脚不知是被磨的还是被石头路给烫的,起了个大水泡,我顺手拔来一把发烫的卷成条的蒙干草,将鞋子绑了起来,手指对面半山腰说,如果在对面挖一个山洞那边就到王宅了,我们就不用爬山岭了。
“别做梦了,继续挑吧!”阿宽说。我们个个很怕扁担碰肩,苏东的肩膀已经磨破了皮,他只想哭,但又不得不挑,肩膀裂开似的疼,双脚像是浇灌了铅一样,肩上的重担,压得我们迈不了步,大地的热浪,烤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路上没有行人,因为人们都知道,夏天午后的日头,后妈的拳头——毒。再说,这条10里长岭不知何故,仅仅只有林坑崖背三颗树可以遮阳。唯独只有我们四个初生牛犊,仍然艰难地用拄杖拄着一步一步跨上一个一个没完没了的台阶。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挑到了际坳塘岭头,汗水也流干了,每个人的背上留下的都是圈圈白色的地图——盐霜。
夕阳西下的黄坦,是那么的美丽动人,我们像是久别了的婴儿,恨不得立即扑向母亲的怀抱。那种胜利在望、幸福、自豪的感觉,顿时,扬在个个人的脸上,什么烈日、疼痛、疲惫、饥渴,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很快,我们下了际坳岭。
到了王宅供销社,我以胜利者的姿态满怀喜悦地把出货单递给了供销社叔叔,他看了看单子,叫我们把盐过磅,结果,我们各人都少了五斤左右,我们都惊呆了。叔叔还说要我们赔,那还了得,当时每斤盐的价格是一角三分五,那我们每人都不是要赔上六七角钱了吗,挑的工钱每百斤是九角七分,那我们的工资还不够赔呀。
我们望着那被太阳晒的白花花的两袋盐,发呆、迷茫、沮丧、欲哭无泪,心里的难受,远远掩盖了一天的疲惫,一双双苦苦哀求的眼神投向叔叔,“盐又吃不得,怎么会少了呢?”小林委屈地流着眼泪说。叔叔开口了,说:“那看在你们年少的分上,赔就免了,可你们的挑运的工资可没有办法给了哟。” 我们很无奈,垂头丧气地拿着空空的扁担挑着空空的饭包,带着一颗满满疑虑又颤抖的心,迈着蹒跚的步履,不知回家跟父母如何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