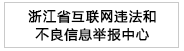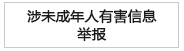攀门台旧事
郑杨松岁月流逝,攀门台早已物是人非。坐落在林店尾的攀门台,过去是大宅院,如今既非街,也非巷,既非墩,也非台,是一个居民区。
拂去新楼台的重重迷雾,显露岀这座宅院的美丽与雄奇,在世的人都没见过这座大宅院,但大宅院的天井道坦与攀门台的断壁残垣及门廊楼台遗址,就连上世纪80年代出世的人也见过,号称林店尾大宅院,绝非空穴来风。攀门台上靠王宅四合院,下临门前溪,东依大峃街,西面周村塅,5千多平方米的遗址石条石阶,围墙内的上下两个天井道坦,足让人依稀记得当年钟鸣鼎食人家的辉煌。呈方型的天井四周全是丈余的花岗岩石条铺成,石阶下的天井由大小一样发光的石子凑成阴阳八卦图案,八卦图案外是无数个回字型图案,左右对称,角度平衡。那时我们都还小,谁都不懂这个图案是什么意思。这个天井约一百平方米,上得石阶来,左右都是厢房遗址,正面是前厅后厅,在前厅与后厅之间又有一个天井,可惜后人没见过楼台,空留下一大一小一上一下的两个天井,见证攀门台的兴衰历史。
这些厢房地基被后人隔成一块块菜地。只有两个天井保持得完好无损,被大家公用,作为道坦道路与晒谷坪。我想,上天井全是花岗岩,下天井有美丽的八卦图案,这恐怕是先人布下迷魂阵,人们不忍或不敢下手罢了。从两个天井可以看岀,攀门台当年是何等气派。宅院的主人决非等闲之辈寻常百姓家,非官即商,非富即贵,经多方打听,结合当年阿爷(祖父)的传说,攀门台的前世今生终于露出水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亏我还是土生土长的攀门台人,攀门台系林店尾的陈姓所建,是大财主大商人,祖上是瑞安平阳一带的盐商舵主。家中十分富有,这盐商舵主的公子,看上平阳知县师爷的千金小姐,托媒说合,这师爷一听女婿是大峃山头人,遂不允婚,这陈氏也生气了,小小七品的师爷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不捐官,捐个七品并非难事。但他没有买官,他要在大峃建一幢比平阳县衙还要气派的房子,于是从平阳请来最有名的风水先生,在大峃选风水宝地,并请来远近有名的能工巧匠,在这里大兴土木,经过几年奋斗,一座四合院建成,在建门廊时,这风水先生提议取名“攀门台”。乔迁后又托媒向平阳师爷提亲,师爷为陈氏的真情所动,终于允婚。完婚后这陈氏的盐业生意是做得风生水起,市场扩展到平阳一带。这平阳也有一盐业舵主,闻知大峃人在平阳抢市场争生意,那还了得,后来打听到,大峃盐商舵主是平阳师爷的亲家,一个平时偷税漏税的商人怎敢得罪师爷,于是只得忍了,表面上忍了,暗地里已经结下梁子,后来这个平阳盐商舵主参加了平阳帮派组织“金钱会”。
同治年间(1866)太平天国被清兵战败,残部南下到平阳与当地金钱会称兄道弟互相勾结,平阳金钱会的头目怂恿太平天国残部(那时当地人称长毛反)兵发大峃攀门台,把宅院里的老少集中在天井里,搜光所有人身上值钱的东西,然后赶出院外,兵丁入内翻箱倒柜把所有金银财宝洗劫一空。临出门点火烧了大宅院。那时的楼台全是木头结构,虽然雕龙刻凤,但干柴烈火顷刻间成火海,陈氏苦心经营的攀门台,倾刻间化为灰烬。陈氏一脉不知所踪。到了上世纪40年代,林店尾乡绅郑志学在攀门台后院的地基上建了一幢房子,吴鸣皋在攀门台上首建了一幢房子,陈德文在攀门台下首建了一幢房子,其他的遗址宅基被附近的人家开垦成菜地。这三户人家成了鼎角之势,攀门台自古就是人才蔚起的地方,大宅院的楼台虽然没有了,但留下了门廊与断壁残垣天井道坦,成为林店尾人公共活动的场所,许多活动都在这里上演,上世纪50年代的斗地主分田地,过年的舞龙灯,民间剧团的排戏都在这里。
一代乡贤吴鸣皋先生就住在这里,吴先生是干事业的人,名气大,很少在家里,这里要说的是吴师母。吴师母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新中国成立前吴先生办了一个《莺湖学社》私塾,吴先生自任校长教师,来读书的穷青少年都是免费的,有的还要赠书本费,其开支全靠吴师母支撑着,这个学社,只有支岀,没有收入,吴师母从无怨言。新中国成立后莺湖学社解散,学生分流到各公立学校。上世纪60年代,吴先生的得意学生周丹臣考上浙江大学,这周丹臣父亲早亡,母亲供他读书已是债台高筑,拿到通知书时哭了,母亲根本拿不岀钱供儿子上大学。吴师母得知后,毫不犹豫拿岀自己的钱,支持这位穷学生上大学。
二十世纪50年代土改时,吴师母家中颇有些田地,雇过长工,收过租,土改工作队根据吴师母的情况定为地主成分,政策落实后,引起群众议论,有人认为,吴师母一生乐善好施,她过的生活与普通穷苦人家一样,要求纠正,工作队深入调查,吴师母家果然很穷。工作队长说,你收的田租都到哪里去了,吴师母说,你去问问佃户就知道了。工作队到佃户家查询,方知他种了吴师母的田,根本就没有收租,佃户很过意不去,过年时给吴师母送去一只鸡或年糕之类的,吴师母总是有东西回赠,且回赠的价钱远不止一只鸡。佃户说,似吴师母这样的人,不要说田地不多,就是百亩良田,也富不起来。工作队认为,这还是一面之词,于是到吴师母家看看,吴师母家果然没有一样是值钱的,就连房子也是土墙的,于是将吴师母家的特殊情况向上级汇报,最后的结论是,吴师母虽然没有田租收入,但她的田地没有送人的契字,田地还是她的,成分还是地主,但不影响吴先生的工作前途和子女读书升学的机会。在那个年代,吴师母能得到如此礼遇,也算好人有好报了。
改革开放后,吴师母的子女事业有成,认为老母亲虽身为地主,但在物质方面没享受过地主的待遇,于是每月寄钱给母亲,叫她不要委屈了自己。吴师母不改勤俭家风,总是不乱花钱。攀门台人认为,吴先生与吴师母的钱,就是大家的钱,都会用在大家身上。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吴先生在岩庵风景区、百丈漈风景区、林店尾山等地建凉亭,还建文成县人民医院住院部的前廊,其身后离不开吴师母的支持。在建林店尾山凉亭时,吴先生已经没有钱了,他知道吴师母身上还有儿子给他的钱,便向老伴借用,说是林店尾山这个凉亭用吴师母的名义建,吴师母笑着对丈夫说,你一生向我借过多少次钱,哪一次有还,从新中国成立前办莺湖学社,支持穷学生读书起,到你岀那么多书,哪一次没向我借?我这个地主就是让你借穷了。这倒是事实。吴先生每次向吴师母要钱,吴师母总是倾其所有,积极支持吴先生的公益事业,当吴先生说要与吴师母建亭立碑时,吴师母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支持公益事业是我的本分。”吴师母的好施乐助精神,潜移默化感染了他们的学生,当年的莺湖学社学生王绍基在建设岩庵风景区时,投入几十万元,周元平在抗疫时捐款2万元。吴先生是名人,各界冠以吴先生为“一代乡贤”,但吴师母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吴先生去世后,当年莺湖学社的学生,一如既往地敬重这位德高望重的吴师母,吴师母好心得长寿,去世那年刚好一百岁。80岁的王绍基泣不成声地说:“我的老师母,世上无双。”周元平说:“我一生最高兴的事,就是遇上这么好的师母。”吴师母是攀门台人的骄傲。攀门台下首住着打银匠陈德文一家,他的后院有一丛湘妃竹(大峃人叫了丝竹),竹旁有一棵很大的柚子树,在竹与树之间有一副棺材,棺材放在凳子上,上面盖了茅草,最招人喜欢的就是那棵挂满柚子的树,最让人怕的就是那副棺材。柚子是饿昏了的少年的最爱,而棺材是那个迷信年代的忌讳,这是一棵早熟的柚子,柚子开花的时候招蜂引蝶,柚子成熟的时候引人招偷。在那食物十分匮乏的年代,人们对这棵挂满柚子的大树垂涎欲滴。特别是饿得瘦骨嶙峋的少年,总打起偷摘柚子的主意。
但最讨厌的是那副盖了茅草的棺材,看了让人胆战心惊,那个年代,林店尾人还是相当迷信的,物质生活内容谈得最多的是吃东西,精神生活内容谈得最多的就是鬼神。因此谈鬼色变,而且棺材是与死人联系在一起的,死人又与鬼缠在一起,几次打起偷陈德文家的柚的主意,但都被棺材里的鬼吓住了。
这鬼来无影去无踪,谁知棺材里会不会伸岀一只手来,那时我们都很嘴馋,又是饥饿难挡,饿死不如被鬼吓死。年纪大一点的陈德高狗胆包天,他说不要怕,陈德文打银眼睛被火熏坏了,根本走不动,他家的几个儿子都还小,只有阿英大一点,也根本抓不住我们。听德高一分析,偷柚的决心更大了,现在就怕那副棺材,里边是不是真有死人。德高的主意多,他说:“听说古铜钱能压邪,每个人身上装了古铜钱就不怕鬼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开始实施偷柚计划了,我们三人先是踩点,由哪里进去,由哪里出来。由德高上树,由全根看守陈德文家的动静,由我看着那副棺材。一百次计划抵不上一次实干,德高很快上树,很快摘柚下来,真是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得手后跑到泗洲桥下剥皮分柚,这次摘了两个柚子,那甜中带酸的味道好极了。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更顺利,那棺材里既然没有鬼,屋里的陈德文根本听不到,用不着前怕人后怕鬼,都是自己吓自己。第三次摘抽时,德高说:“我们摘一个柚子是偷,摘十个也是偷,干脆多摘几个。”这一次德高不要我们看德文家的动静,也不要看棺材,他把柚子丢下来,要我们在地上捡。我们都听他的。德高上树后,把柚子丢下来,不小心把一个柚子重重地砸在棺材的盖上,“哐”的一声巨响。“谁在偷柚。”随着响声,德文的女儿阿英出现在我们面前,德高躲在树上不敢下来了,阿英指着我和全根说:“看不出来,你们是偷柚的贼。”我们说,不是我们摘的。“还有谁?”我们指了指树上,德高见躲不过,从树上跳下来了,这德高年纪虽比阿英小,但辈分高,还是阿英的堂叔呢,阿英说:“想不到小叔叔还是贼头呢。”我们忙说,阿英姐,我们下次不敢了。那个全根见我叫阿英姐,也乱叫起阿英姐来。阿英对全根说,你年龄虽然比我小,论辈分,我要叫你阿公呢。全根忙说:“阿公给你赔不是了。”阿英是菩萨心肠,见我瘦得皮包骨,不但没有骂我们,还把地上的柚子捡起来送给我们,对德高说,你慌里慌张上树,万一跌下来怎么办。德高嘴甜说:“你好人有好报。”第二年,17岁的阿英被群众推选为村里的妇女主任。后来我们都懂事了,也长大了,与阿英姐之间彼此都很友好,我问阿英,柚子树下的棺材是不是装了死人?阿英说,那是她阿娘(奶奶)的寿材,放在家里,小孩会怕,又没地方放,只好放在柚子树下,上面盖茅草是怕日晒雨淋,外人以为是没有下葬的棺材。不过那副空棺材还真的起了一定作用,在那个物质匮乏,盗贼四起的年代,阿英家的打银店,从未遭过贼偷。原来阿英家是虚张声势演的空城计,攀门台人既仗义也足智多谋。
现在在的攀门台,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建筑,只有攀门台1号楼是上世纪40年代的旧物,现在已成危房,已经闲置20来年了,我5岁随阿娘在这里居住,为了写此文,溯源那尘封的往事,我又回到这里。推开那扇破旧的老门,一股霉气扑鼻而来,多年没有人气的老屋,依然堆满旧物件,我在寻找阿娘用过的旧物,居然一件都没有。阿娘是三寸金莲缠脚女人,她不但断文识字,更是纺纱织布的能人,阿娘16岁嫁我阿爷(祖父),过门以后整天伴随着纺车与织布机,一年中有9个月纺纱,3个月织布。在那个年代自家备有纺车与织布机,应是有些来头的人家,阿娘是大峃王合吉商号的千金,王合吉商号遍布瑞安温州,阿娘过门后,娘家的父兄都迁往温州。阿娘小脚,去温州需坐轿,因此阿娘过门以后就很少走动,阿娘四季都与棉花、纺车、织布机朝夕相处,根本不像财主家的千金。
夏日的早晨,阿娘要纺一个纱锭的纱;隆冬的夜晚,在那一盞如豆的油灯下,阿娘每夜要织5尺布。我5岁跟阿娘睡,阿娘总是叫我先睡,她自己坐在纺车前,把身影投落在墙壁上,低着头,右手摇动着纺车的摇把,左手三指捏着那细长的棉条,从低处转动着的锭针处,慢慢地拉张开来,手臂一直向后斜斜地舒展开去,直到伸直,随着右手将摇柄反复转动......我到半夜醒来,听到那纺车单调的吱吱声,叫阿娘快睡,阿娘总是说,忙完手中的,马上就来。阿娘是出了名的纺纱好手,纺出的纱又细又均匀,谁家的新媳妇在纺纱中遇到难题,找阿娘帮忙,阿娘总是热情相帮。
阿娘心灵手巧,不但会织普通的平布,也会织有格子的花纹布,速度之快,难以置信。电影“七仙女”里,财主要仙女一夜工夫用乱纱织成百匹绸缎,仙女点起难香从天上请来七个姐妹下凡,施用法术,一夜完成,那是神话。而阿娘夜织一丈布,那是家常便饭,林店尾人都知道,阿娘是三寸金莲小脚,但织起布来,脚下生风。穿梭引线快如飞,如果织格子花纹布,阿娘用的是双梭,这是阿娘的绝技,她坐在织布机前,手脚不停地忙碌着,但不会手忙脚乱,手有序,脚有律,上面一手拉动织梭,一手来回拉着扣机,把织进的棉纱扣紧,而下面的两脚踩着踏板,把纬线上下不停地错开,好让梭子带回经线,来回编织。阿娘织的布平整没有疙瘩,加上染色得体,做的衣服棱角分明,质感上显得厚实而粗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家都穿阿娘织的布,后来上级要求农村“种植以粮为纲”,再则市场上推行机器织的布,慢慢地纺纱与织布都销声匿迹了,阿娘在一阵阵远去的机杼声里,纺弯了腰,织白了头,攀门台再也寻不到纺纱织布人了。 攀门台的上下两个天井,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纪8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人们终于对这块垂涎已久的风水宝地动手了,一夜之间,先人布下的阴阳八卦阵,被挖掘机挖得七零八落,接着牵绳拉线打桩,几年后高楼林立,攀门台大宅院永远消失了,但攀门台的名字不会消失,那是攀门台人农耕生活中的一缕旧事乡愁。